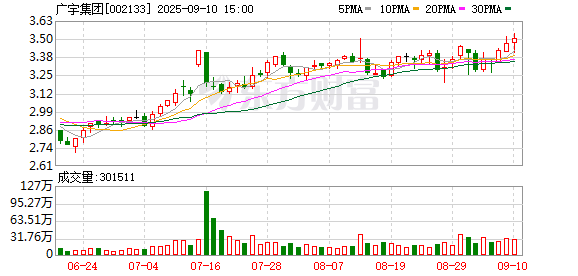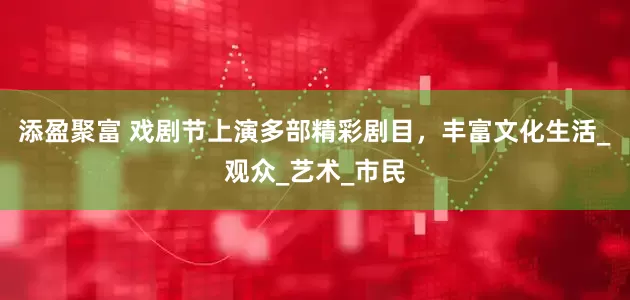“1982年6月15日午后,小赵优配无忧,这位副团长叫什么?”在营房门口低声发问,汗水顺着军帽檐滴落。
军区司令难得现身基层,他用扫射般的目光端详眼前的年轻军官,那张脸越看越熟。端礼毕,车队即将发动,他却突然站住脚,扭头回喊:“把那副团长叫来,我再看看。”随从面面相觑,只得照办。
另一次细看,他依旧肯定自己以前见过这副团长,但一时想不起名字。等听到师长汇报“吴崇德,炮兵副团长,江苏人”,他心里猛地咯噔一下,嘴角几乎同时蹦出一句闷雷似的低语:“糟了,大事不好!”声音虽小,却足以让身边的作训参谋瞪大了眼。

巡察行程紧凑,他在车上翻出作息本,迅速拨通电话。“老首长,你怎么把孩子丢基层也不告诉我?”另一端,吴克华哈哈大笑。“他是我儿子没错,可在队伍里就是个兵。别给我添麻烦,别提前提拔!”尤太忠揉着眉心,无奈又佩服。
认识吴克华不是一天两天。早在1947年八月,他带十六旅死守大雷岗,为全军渡汝河争取时间。那一昼夜,伤亡两千,通讯员用弹药箱当担架运走牺牲者。“天地都在抖,”他事后叹,“人一裹毯子就埋,下不去泪。”可他记得每个人的名字。
对指挥员而言,地图就是生命。抗美援朝时他文化底子薄,却能对着密密麻麻的朝鲜地名脱口而出。夫人王雪晨半夜拿着电筒临考,他次次答对。“别人用笔记,我用心记,”他说,“打仗差一寸,死一排兄弟,敢马虎?”
除了谨慎,他还有股子仗义劲。1949年冬雨连绵,三兵团准备攻入重庆,他与士兵同淋一夜。有人劝他去屋檐下躲一躲,他摇头:“战士湿,我也湿。”许世友去世后,他自掏腰包从广西买回两段百年楠木优配无忧,直送南京做棺材;王近山被下放,连朋友都躲,他却连夜赶去车站迎人。

1973年春,邓小平刚被允许回京,屋里除了残茶就是纸烟。他拧开门,递过去五条“中华”。邓小平接过,用力吸了一口,半开玩笑说:“老尤,你总是惹事。”他笑:“您永远是我的政委。”
因此,吴崇德突然出现在自己军区,才让他如坐针毡——官兵认可这个青年,可若因父辈光环被提前提拔,不仅坏了规矩,也坏了两位老战友的清白。电话里他一句“你放心,我心里有数”,算是给吴克华吃了定心丸。
说到吴克华,这位解放军炮兵司令、新疆、成都两大军区主官,骨子里最重的却是“孝”字。父亲早逝,他七岁便跟母亲相依为命。1931年春,赣东北苏区被敌人围堵,他在前线打仗,母亲因“小脚走不快”被敌军抓住。敌人逼她写信叫儿子投降,她冷笑:“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”当晚,刽子手行刑。

消息传到前线,他跑回家乡,抱着母亲残缺的遗体嚎啕。草草掩埋后,他在坟前立誓:“日后若有一息,全给穷人出气,也给母亲讨债。”这份恨,后来化作枪口的火舌。
转战十数年,他与许世友在胶东、莱芜并肩作战。胶东一役,司令部驻村仅六十户,为护乡亲,两人带警卫队挨家劝迁。十六位母亲带着儿子报名参军的场景,他提起多次:“乡亲们把孩子交给咱,咱就得给个交代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,他不求享受,却坚持一件事:给母亲扫墓。从新疆回赣东北路途极远,他一请假就往山里跑。墓前话不多,只有一捧黄土。他啃干粮,坐半天。战友打趣:“司令也艰苦朴素。”他摆手:“在娘面前,啥司令?”
1987年2月,病危的他留下薄薄一页遗嘱:“塔山阻击,战友长眠;余亦愿同眠。”儿女红了眼眶,却知道拗不过。翌年“八一”,他们把骨灰撤进塔山的风里。山下渔火点点,老兵说:“炮司令回来了。”

家乡乡亲没忘记这位烈骨硬汉,在他母亲的坟顶修了一座纪念亭。塑像穿戎装,面朝东南,像在守望那条母子曾经逃不出的山路。
回到1982年,吴崇德依旧在基层带兵。岗位没变,待遇没变,唯独多了份无形的压力——他的姓氏提醒自己,犯错不仅丢个人的脸,还会砸父辈的牌子。多年以后他回忆:“尤司令那句‘大事不好’,其实是提醒我,走歪一步都不行。”
不得不说,那幕尴尬的午后,折射的是军队内部对清正的极高期待。将领子弟能否脱掉光环靠业绩说话,父辈能否抵住亲情考验,这样的故事过去有,以后也不会少。规矩立在那里,兵心就安。
飚升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