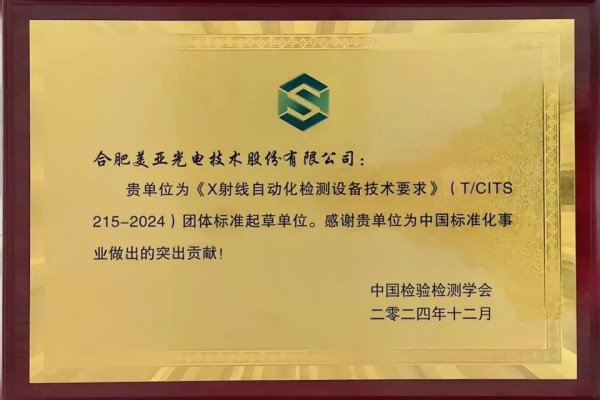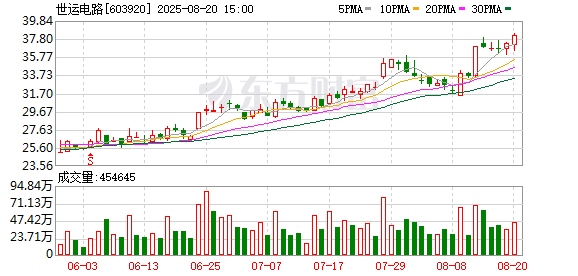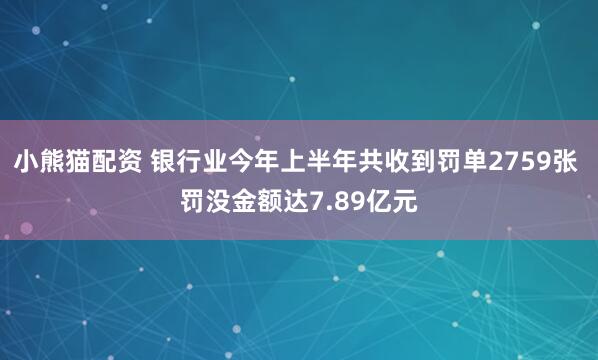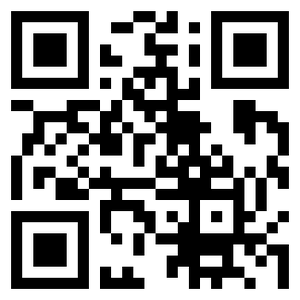1943年2月,在山东抗日根据地,八路军经过一场伏击战后成功缴获了两挺九二式重机枪。这些武器对于八路军来说无疑是极为宝贵的,因为他们在长期的抗战中,重火力的缺乏始终是一个困扰。八路军的战士们不敢掉以轻心东方优配,小心翼翼地擦拭枪身,精心保养。然而,这些重机枪虽然得到了很好的保养,却因为缺乏适配的子弹而无法发挥作用。机枪手们围着空空如也的枪身,焦虑万分,心中只有一个问题:没有子弹,这些重机枪究竟有何用?鲁南军区联络部部长廉纯一在作战日志中写道:“机枪无法使用,战士们十分焦急。”
然而,百里之外的徐州城内,铜山火车站旁的日军军火库,却恰好储存着八路军急需的机枪子弹。这个军火库有着极其严密的守卫,城墙高耸,哨卡四处设立,甚至有巡逻队日夜守卫,想强行突破几乎没有任何可能。然而,三天后,廉纯一到达了后姚村,开始了新的工作。当他在田埂上稍作休息时,和村民张士钊聊起了这件事。廉纯一感叹道:“如果能弄到一些机枪子弹就好了。”张士钊听到后,立刻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,认真的说道:“我有办法试试。”廉纯一有些疑惑,甚至认为他只是在开玩笑,但张士钊却一脸真诚地说:“打鬼子不一定非得靠枪,你们等着看我怎么做。”
说干就干,张士钊立刻联系了杜全德,徐州城内拉板车的商人。杜全德的家靠近日军的军火库,两人曾经在货运时有过一些交情。第二天清晨,张士钊牵着牛走出村,告诉妻子他要进城拜访朋友,便踏上了前往徐州的路。牛铃响个不停,寒冷的土路上留下了他的脚步声。到了徐州西城区,杜全德见到了久别的老友张士钊,听完他的计划后,他紧紧握住张士钊的手臂,坚决道:“这事我来做!”
展开剩余76%两人推着空板车,绕过军火库的外墙,细心地观察每一处可能的突破点。转到仓库西北角时,他们发现墙边杂草丛生,生长到足以遮掩他们的行踪。杜全德扒开藤蔓,竟然发现了一处半人高的狗洞,洞口处用铁条封住。张士钊摸着锈迹斑斑的铁条,低声说道:“机会来了!”然而,远处突然传来巡逻队的脚步声,二人赶紧蹲下,装作修车。夜幕降临,两人将钢锯和麻绳藏进板车夹层。
寒风刺骨的子时,张士钊和杜全德悄悄来到了狗洞旁,开始用钢锯锯断铁条。锯齿与铁条摩擦发出的声音和寒风交织在一起,每次停下来,他们都会小心地观察四周东方优配,确保没有被发现。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,铁条终于被锯断。张士钊趴下身子,钻进了黑暗的洞内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机油味,他摸索着找到了几堆木箱,便开始将箱子拖出来。墙外的杜全德接应着,迅速把箱子传递到牛车上,最后用空箱堵住了洞口。两人迅速撤离,趁着黎明的薄雾隐匿在其中。
弹药被暂时存放在杜全德家的柴房里,但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城门的检查。由于日军严格搜查过往的车辆,草席遮盖的车身很容易暴露。张士钊苦思冥想,却突然看到杜全德提着粪桶从家里走了出来。一小时后,他拎着两桶臭气熏天的粪水回到家,站在车旁对张士钊说:“泼上去,鬼子怕臭!”于是,二人把粪水浇在了盖着箱子的草席上,黄水从车缝里滴落。张士钊心生疑虑,担心万一日军要严查怎么办。杜全德抽出鞭子,笑道:“到时抽牛,粪水溅开了,他们根本不敢接近!”
清晨,张士钊驾着牛车混进了出城的队伍。距离城门百米处,日军哨兵一一检查过路的行李和车辆,空气中弥漫着粪臭。轮到他们的车时,哨兵捏着鼻子走近,张士钊赶紧抽打牛臀,牛车猛地前冲,车身摇晃,粪水溅到了哨兵的军裤上。哨兵大骂着挥手赶走了他们,张士钊则稳住牛车,趁机悄悄驶出城门。一路上,冷汗早已湿透他的后背,直到拐过山路,他才敢回头看一眼徐州城的轮廓。
不久后,张士钊将这批弹药送到了鲁中军区,经过清点,共有一万九千发子弹。1943年11月9日,这些子弹终于发挥了作用。当八路军某连的战士在岱崮主峰迎击日军的进攻时,重机枪首次开火。机枪手老王扣动扳机的那一刻,子弹正是张士钊亲手带来的。凭借这批弹药,八路军成功抵挡了十八次日军的进攻,战斗中日军死伤惨重,八路军仅有九人受伤。此战被誉为“岱崮保卫战”,而该连也因此获得了“岱崮连”的荣誉。
1951年秋天,廉纯一作为沂水专署副专员,重回后姚村,拜访了张士钊。当时,张士钊正在晒场上翻玉米,衣服沾满了草屑。廉纯一谈及旧事时,张士钊淡淡一笑,说道:“当年拼命是为了打鬼子,功劳不值一提。”他说完便继续翻动着玉米,脸上没有丝毫的骄傲。廉纯一提起杜全德时,张士钊低头叹息道:“杜全德已经去世,若要表扬,就为他在坟上添点土。”风吹过,谷堆沙沙作响,二人就这样沉默地抽完了旱烟,再也没有提起过荣誉和表彰。
张士钊余生耕作在十二亩土地上,村里人都将他视作普通农民。直到1992年,当临沂修地方志时,工作人员在鲁南军区档案室发现了当年廉纯一的工作笔记,其中写着:“1943年3月,群众张士钊、杜全德智取徐州敌军火十三箱,子弹近两万发。”在调查组找到张士钊时,他已经卧病在床,望着房梁喃喃自语:“杜全德家那堵墙……拆了吧?”
如今,徐州西城区的车水马龙掩盖了过去的历史,原先的军火库早已变成了社区广场。老人们在花坛旁晨练,孩子们在健身器材旁玩耍。唯有那棵老槐树,依旧伫立在角落里,裂纹深深的树皮像是岁月的战甲。当年那条被粪车经过的土路,早已被平整的柏油路面所替代。但岱崮山上的弹痕依旧可见,春风吹过岩缝的呜咽声,仿佛在诉说着一个简单的真理:在民族危难之时东方优配,手握锄头的人,同样能挑起抗争的重担。
发布于:天津市飚升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